《纪念碑》:“一方面是我的重要回忆,同时也是出现在我的作品中的墓碑或者雕像。然而这两层含义反射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物质形态,前者虚空无形,后者坚实具体。”
至品生活 采访/撰文:毛菊丹 部分图片提供:香格纳画廊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影子》局部,2016
大屏幕突然亮了,打破了周围的黑暗,双屏同步的影像开始播放。一面黑底的屏幕上浮出诗一般的文字,另一面则像一个难以出逃的梦,画面里投在墙上树枝摇曳的影子,一个男人的背影,还有女人、背对着观众仿佛在叹息。即使没有配乐,人们似乎能够穿过那些漫长镜头感受到闷热难眠的夏日气息,黏着的汗水以及不绝于耳的蝉鸣,勾勒出某个东南亚国度难耐的炎夏季节。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影子》局部,2016
“这些从1994-2017年中挑选出的作品映射了我从出生地孔敬至我的现居住地清迈的一段旅程以及从泰国东北部其他地方的探索。它展现了我生活中的现实,虚构以及梦想的融合。”
这是泰国艺术家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于上海香格纳画廊开幕的个展——《纪念碑》的现场,观众们都屏息注视着他的这件作品《影子》。除了呼吸之外,划破寂静的只有幻灯机切换画面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透过向前方屏幕投射的光束里起舞的灰尘,阿彼察邦本人站在投影机旁,似乎也在跟着一起再次回味。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俳句》,2009
半梦半醒间,意识闪烁模糊,阿彼察邦承认早上起来的时光对他来说是一天当中最有灵感的时刻,他说人们往往能用刚刚打开的感官捕捉到更为敏感而细腻的事物。与许多热衷于在恢弘历史叙事背景下创作出极具戏剧感的作品、千方百计地调动崇高感的艺术家不同,阿彼察邦的作品更为私人化。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宫殿》,2007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着火的花园》,2016
穿过热带的丛林,偶遇了一个隐匿的私人花园,在这里难以分清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见与不见、实在的空间与虚无交错重叠,如落在围墙上影影绰绰晃动的树影一般,观看阿彼察邦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体验,平稳的节奏燃起了近乎催眠的视觉审美。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Power Boy》,2011
的确,梦境是阿彼察邦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分。主角和观众互相渗透着彼此梦境的作品《影子》就是如此,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金棕榈奖的电影作品《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以及获得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的《热带疾病》也是如此,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艺术家本人对自己故土、亲人的绵长伤感和忧虑。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幻梦墓园》,2015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2010
梦·森林
1970年,阿彼察邦出生于曼谷,后来全家迁至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市。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泰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的内战血腥冲突成了这个国家难以抚平的伤口,也是阿彼察邦记忆深处难以散去的一场噩梦,他想要逃离这个原初记忆的包袱,所以在他很多的作品里都有那么一片森林,灵魂、鬼神、转世、来生,离奇的故事像被来回折射的声波,在森林里荡来荡去。在这片森林里,有抱在一起的两只骷髅,他们被眼前亮闪闪的烟花点亮(《烟火(档案)》);波米叔叔梦到了变成猩猩的儿子在森林里穿梭,亮着红色的眼睛,而他自己转世成为了森林里的大象猎人、水牛、母牛和野鬼(《能找回前世的波米叔叔》)。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烟火(档案)》,2014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2010
“当你在树林里拍摄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自由,那些在影棚里碰到的条条框框将一律不存在,你也会慢慢懂得尊重自然,将注意力放到自然当中,向阳光、时间以及所有的生灵致以敬意,与自然翩跹起舞。”而在这次的个展中,阿彼察邦用红外摄影机拍摄于哥伦比亚的新作品《记忆·丛林》里那个迷失在丛林的男孩,也成为一种隐匿、迷失却又回归本性和自由的象征。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2010
“我十分厌倦曼谷,想尽可能地逃离它。我想找到一条回归故乡的道路,那里透着生机盎然的绿色,保留着我们原初的美好记忆,那里是自由的归宿,皈依本心。”阿彼察邦在自己镜头里频繁出现的森林里藏了一个苦涩而甜蜜的梦,它因为沉重的历史记忆、人们的善良而愚昧以及不断的冲突而苦涩,他想逃离、却又想找寻,矛盾的心境就像热带丛林里的树木,盘根错节,纠缠不清,但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真实的人生写照。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2010
梦·海涛
2013年,阿彼察邦的多年好友、苏格兰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马尔代夫组织了一场朋友聚会,阿彼察邦让她在镜头前回忆自己的梦境。蒂尔达闭着眼,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杂乱的海景中,成了这次展览中的作品《影像日记: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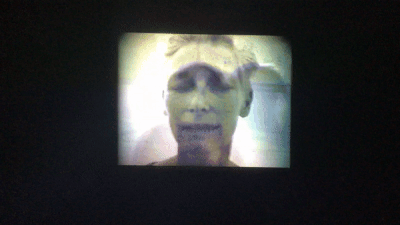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影响日记:一水》,2013
而站在二楼的展厅外,可以听见连绵不绝的清脆的钢琴声,这是他与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合作的作品《async-第一束光》,汽车沿着海边的路道行驶,整屏的海涛翻滚波澜、透着初升的太阳投向海平面的第一束光。阿彼察邦把照相机寄给朋友们,镜头里熟睡的人们都来自他们的自拍。海涛卷着梦境,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浪打上岸、又退却入海,仿佛情绪的高低起伏,没有可以名状的理由、没有任何强词夺理的逼迫,自在地流动于我们的身体里。作为观者,我们见证着这些行动,同时也沉浸于片中悄然弥漫、间接传递的情绪:期盼、焦虑、迷失、缺失、懒散、精力充沛。当我们徘徊在我们真实所见与模糊感受之间,我们被推出熟悉的领域,去追问我们看到的是真实或想象,虚构或纪实,亦或是两者结合。一个一个的梦境、一个一个的冲动,他说这些就像海浪一般席卷着内心挣扎的欲望、潜意识,以及想对别人诉说却无从言语的片段,零星而完整地组成了我们人生的全部。活着,到底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虚构,而又有多少是想象,我们无从得知。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sync-第一束光》,2017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全由过去的记忆塑造。那些发生、经历过的难忘的事,深爱的人,遭遇重创并在修复过程中的心灵,就是我想在我的作品里诉说的全部。”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记忆,皮豪 (埃弗•阿斯图迪略)》,2017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烟火(风扇)》,2016
“如果有来生,你想成为什么?”顺着他的思维流动,我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艺术家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我想要成为一棵树,”面目清秀、性格腼腆的阿彼察邦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也许这正是他想要扎根自然、坚守初心而岿然不动的心境,从建筑师转成艺术家、为自己的同性恋爱抗争,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到未来,也许他一直都会是这样一个人。


